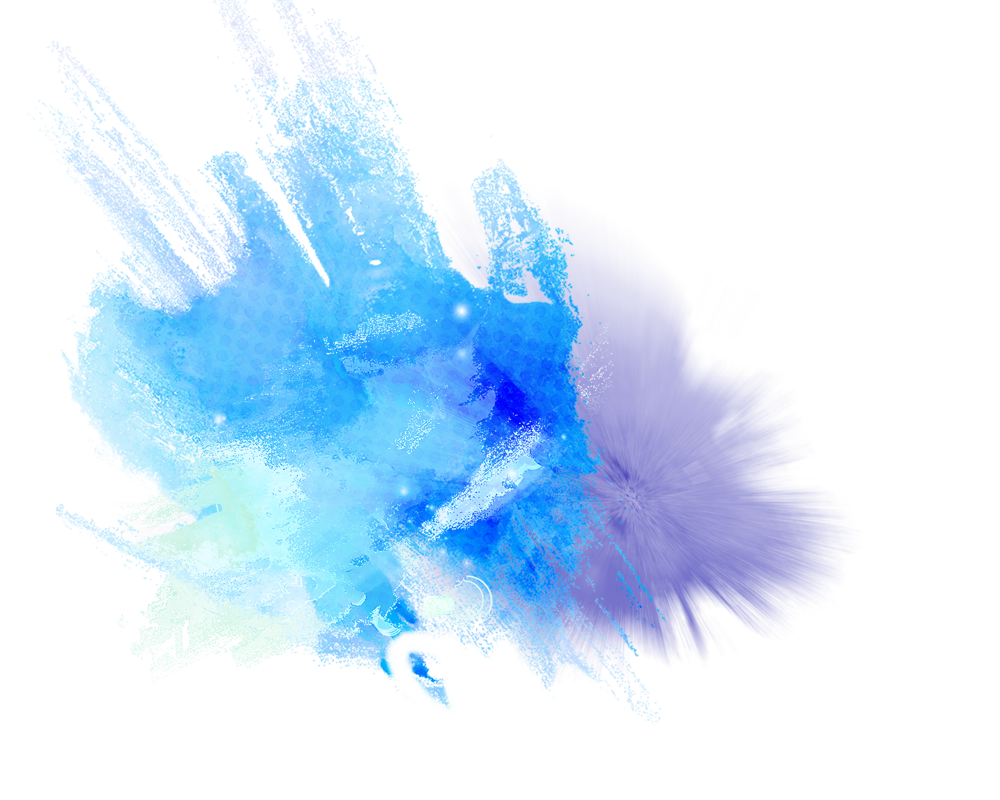在试图找寻初高中教辅丢给妹妹学习的失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历史遗留文档,初二某个假期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哎哟喂,仔细看完之后觉得有必要记录一下子。
没想到初中的我这么有才。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有才吗?我看着字迹,再看篇幅,咋觉得像是我在最后一周敷衍作业的时候,拼接了别人家的读后感呢……从小就是裁缝了?好像还是高级裁缝,自己写一点,别人的话用一点。Anyway,看一下子。
嗯,再回忆,好像真是高级裁缝,先是自己有一版本的腹稿,再去看别人的读后感,之后一气呵成,仅成 300-400 字。嗯,好像确实是这样子的。不像现在能洋洋洒洒几千字,颠来倒去都是废话。
再说一句,初二,我记得那时候还写过小说吧,甚至发了一章节到纵横上去……真真是黑历史,作者号后来高一被我注销了,不过文章内容我倒是还存档了来着。对,我存档了,现在电脑里面有整理过的内容,还不止一本,不过,只有设定和开头。从小就是拖更王者,怎么说,不忘初心了。
还有一件事,看着这作业本,差点认不出自己的笔迹,离谱……我记得是初三中考前夕我改了握笔姿势,运笔什么的大进步之后到现在就是进化成行楷+狂草混搭,但在这之前,字写的有这么烂嘛!?还有这逗号句号打的,纯粹一个点点,好想骂一骂那时候的自己,写的什么玩意儿。辛苦初中老师了,看我一手狗爬字。
我与地坛
地坛这个地方,史铁生自己也说过自己与它有缘,自从他在狂妄的年龄失去了双腿后,十五年间,日日来地坛。很喜欢史铁生娓娓道来的感觉,没有过分的感情波动,只有平淡的叙述,好像他不曾经历过这些一样。可能残疾的病痛使他煎熬,最终,他认清了、看淡了,可隐藏在这颗平淡的心之下,是那历经沧桑的深邃,他接受了,形成了看透红尘的坦然与从容。读完这篇文章,才可以感受史铁生对于地坛这个地方的眷恋与依赖,在他残疾后的最初几年迷茫的日子,这里是他唯一的心灵寄托,他便摇着轮椅来到地坛,在那里久坐。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只有那个颓然的他,摇着轮椅缓缓地停靠在苍黑的古柏树下,一棵落寞的古树,一个孤寂的黑影。
可以说,若是没有见证地坛的花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死,他也不会看清自己的灵魂,他也不会将生死看得如此透彻。只有在地坛,他才能释怀,才能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他将自己内心深处的孤寂忧伤留给了地坛,留给大家的,只有那一抹淡然。
我二十一岁那年
《我二十一岁那年》,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题目,感觉并不是一位大家所作的文章,感觉只是一个朴实、历经沧桑的人所回忆的往事,写下这篇文章,并不为多著名,只为找到一位知己,与其谈心。
开头“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这个地址注定了这个故事的不平凡,但作者却这么平淡地写了下来,足以见得四十岁的他已经完全看淡了。对很多人来说,二十一岁,是年轻狂妄的岁月,是充满青春与朝气的年华,可岁月与命运这两位雕塑家,沉着而冷静地刻写着人们的结局,它们的作品往往出其不意地展现在你面前,使你目瞪口呆。
对史铁生来说,二十一岁的厄运突降,让他的青春天崩地陷般毁灭,双腿瘫痪的他在一次次希望与绝望的万丈落差之中已经被打落在地无数次,但他却顽强地挺了过来,书中的一个个文字,背后是他血与泪的回忆。四十岁的他写下这篇文章,文字不是很华美的风花雪月,只有平淡的娓娓道来,但这份平静背后,又有多少血泪心酸;平静的文字下,隐藏着一颗渴望站起来的热血之心,但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他也在这份苦难中感悟、收获、平静。锋利的厄运以岁月削平了他外放的锋芒,留下的却是内敛的睿智与深邃。
就如这样一句话:从绝望中劈出希望之后,人生终将辉煌!
记忆与印象 01
“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已经熄灭,他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过他的青年时光。”史铁生便是如此。
命运总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
十九岁的劫难给了他一副残败的身子。残废的最初几年,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处,忽然间什么都找不到了。黑暗似深渊一般将风华正茂的他裹挟而去,他也不想睁开眼睛去寻找一隙亮光。
他常常一个人摇着轮椅到地坛去玩,于杂草荒芜的园子,某个角落,一连几个小时专心地想关于死地事。就这样寂寞好几年,他终于说服自己,“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他开始平静地去回忆,寂寞地去思考。
我从那些坦白的文字中,从他絮叨的往事中看到了另一个史铁生。他关切地走近那个困顿中的自己,对他劝说与开导。他静静地思考着他的生与死、苦难与信仰等深邃难懂的问题:他发现身体被固定在轮椅上,心可以无比自在地飞翔;肉体被折磨得残破不堪,精神还可以纵横驰骋!
夕阳也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遍布烈阳朝晖之时。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片古老而又贫瘠的土地给了他病残的双腿,他却如此平静甚至诙谐地讲述那里古老的文化、劳苦的生活、朴实的汉子……
如此寂寞的史铁生让人敬重——失去了双腿,却历练了坚强的心!
记忆与印象 02
生死,似乎是一个不可辨驳的永恒话题,没有哪个人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的来临。
而只有一个人,那是品尽了痛苦的滋味,在死神手中挣扎的人——史铁生。
在他躁动不安、纷繁冗杂的尘事中,惟独写作拉远了他与死神的距离。追溯到孩提时代,以现在的心境、平静的口吻描绘出对死神近乎调侃的字字句句。真正领悟到生与死,是在他得病后的那段时光中,“死”无时无刻不泛滥在他的脑海中。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从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他就已经开始死了,只是有的人死的过程短,有的人过程长。“轻轻地 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史铁生借徐志摩的话阐述出对待死亡真正的态度,豁达地面对人生、面对生死。生既是死,死既是生,生与死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有的人说:生比死更困难、更痛苦。史铁生对于死还有一种体会。拖着一副残破的躯壳,放纵灵魂茫然飘逝,实则也是玷污了生与死的名节。生相对于死,死是一种高贵的精神的产物,与其邋遢地活着,不如洁净地死去。对于死,应该是一种凤凰涅槃地重生,是没有形体的负重。
对于死,在经历一次次的生死抉择后,史铁生已不再畏惧,他的思想已不会再受死神的束缚,他的人生,将是一部超越生死界限的无字书。
尾
看完了,大家什么感受?
反正我脚趾抠地,看得特别难受,打字过程也特别难受。喜欢用一些大词,浮于表面的华丽,一股青春疼痛的气息。但我也承认,那时候写东西是有灵气的、有思考的。可能不是那么注重逻辑,感受确是很明显,且能比较准确表达出部分脑子里的想法。
再看现在写文章。“虽然……但是……”“尽管……还……”“但/但是……”“确实”“可能”“还是”“真是”等词,翻来覆去反复用;口语词汇出现频次直线上升。好像句子里没有了转折、术语,一句话就不会写了一样。纯口语化文字除外。
开始思考为什么。
其实这才是我写这篇的目的,自己的文字能力似乎退步了,进入到了“词穷”,或称无法准确表达自我想法的时刻。可我往往同时又有拿笔写下所想的欲望,这种在欲念中挣扎的感觉,也算是我的常态了。总归还是会难受的。
我想这是现代教育体系下的每个个体的必经之路,尤其我尚且算是被训练有素的那一批。也庆幸自己是被训练得比较好的这批人,我有足够的能力、资源与想法去追求一些超越“基本”的东西。可能就是靠着这些东西活着的吧。
彼时彼刻,我可能正在心里审判他者的文化造诣,嗤之以鼻;此时此刻,我成为被审判者,被嘲弄者。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或是短平快视频的成熟,或是算法推荐的成熟,或是温水煮熟的那只青蛙装睡不愿醒,或是易得的多巴胺刺激……总之,我现在成为了曾经我最讨厌的一类人中的一份子。
从什么时候意识到的呢?
在每一次提笔写下感受之时,在每一次开始撰写论文之前,在每一篇课堂作业背后,在偶然提笔想创造世界之际,在和人交谈发现描绘不出自己的瞬间,在再次看到曾经的自己。人生这一部无字书,我已写下了二十多年,现在被写成了一张正态分布。讲不清楚我想到这么个比喻时究竟在想些什么,自嘲?遗憾?有趣?也许都有。亦或没有。
再回过头,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在我写下对大学的一些思考那篇推文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了。掐指一算,预初至大四,不过区区十年左右,骤觉漫长,它占据了已历人生的二分之一;把比较维度拉长了看,又觉短暂。一路历经中考、高考、毕业,其中夹杂无数大小考和测验,思想活跃清晰、认知广度深度的巅峰好像就这么停留在了高中。也是提前步入“回忆青春过去”的年纪(bushi)
可是再细想,此刻的思维与认知明显更加成熟,人又为什么会去怀念那段时光?因为那段时光单纯,不必真正面对生活的复杂。“人是靠回忆过去活着的”,现在的生活显然比那段时光更复杂了,想要活得更简单一些。简单与复杂的天平上,被我放置了不同重量的筹码,我想过怎样的生活,取决于手中握有多少筹码。
继续思考吧,持续思考吧。既没有打破规则的能力,就把自己打磨得更适应规则,直至利用它。